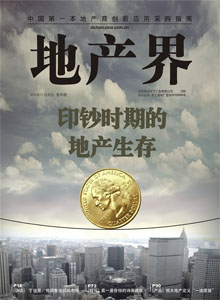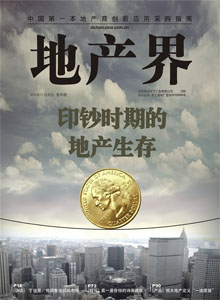【折衷亦另类乎?--记重庆北碚大学科技园主楼方案】
文/中鸿设计 潘彤
我们,生长在新中国的建筑设计师,一般来说受到过两种深刻的教育:一,共产主义革命教育,即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。二,现代建筑教育,即“少就是多”,“装饰即罪恶”等现代主义建筑理论。这两种教育之不可磨灭,已完全渗入我们理解、思考和改变现实的基本框架;形成了某些不可突破的条条框框。——或曰:世界观。
所以,对我们来说,有的路线是完全不可以选择的。比如你可以选择毛泽东或者蒋介石,鲁迅或者胡适,但你肯定不能选择汪精卫,不能选择周作人。
说到建筑,那就是你不能选择折衷主义——那是最糟糕的一种路线。它表明你没有立场:在这一点上,你甚至还不如反革命。
所以,重庆北碚科技园的主楼,其本质是一个与我的世界观相冲突的作品。
这个作品的产生,一方面是由于重庆市领导的特殊喜好;另一方面也证明中国当代文化的多元化已经达到了某种极限。——极限就意味着突破,所以,探讨一种突破基本底线的设计,似乎也是有意义的。
谈到这个建筑的风格,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。在1950~1960年代,我的老系主任梁思成先生还曾经大力提倡过它。它产生于1920~1940年代,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建筑师们普遍采用的风格。所以,我称之为“民国风格”。
1920年代,折衷主义正盛行于西方,于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现代建筑物如北大校园、南京中山陵等,就被美国的墨菲、中国的吕彦直杨廷宝等人以拿来主义的方式设计成了这么一种风格:以典型的对称布局和西洋古典比例作为其基本骨架,以典型的折衷主义作为其设计手法,加入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局部(如大屋顶、额枋彩画、莲花底座纹等等)为其形象上的独特元素。
它和现代主义背道而驰,但也不同于完全的复古。它是一种充满复古精神的中间路线。在现代建筑大行其道的今天,它这种没有立场的中庸,反而显得很另类。
所以,虽然它的本质——折衷主义——是我所不能认同的,而且它也绝对的不先进和不创新,但是在这种风格中,现代建筑所丢失的一些东西被找回来了:堂皇,典雅,细致,以及民族性。
好像是马克思或者列宁,说过这么一段话,大意是:资本主义代替了封建主义,然后资本主义会导致社会主义,因为工人阶级会成为社会气质的主流。结论就是让我们鄙视和嘲笑那些贵族式的气息吧,他们是腐朽和没落的。
我认为革命导师们的看法是相当的一针见血。所以现代主义建筑,其气质就是工人阶级的。就是必须可以重复化机械化地被生产出来,因此必须简洁并且抛弃手工化的小情调,因此必须创造出一种简单之中的美感并且在大众中推广之。——你可以马上联想到一块塑料格子布,一瓶啤酒,和一位机修工人兄弟,脸上洋溢着纯朴的喜悦。而复古的或者折衷主义的建筑,其气质是封建贵族阶级的,就是典雅,堂皇,注重仪表而轻视功能,注重情调而忽视成本。——你可以联想到一块走得很不准的怀表,一顶礼帽,一副忧郁的脸以及皱着的眉头,因为这种人与现实世界差距太大。
回到具体的建筑本身。北碚大学科技园的主楼,其实就是把一栋5万平方米,20层的现代高层写字楼,分散开来,变成4-12层的一组半围合的建筑群。它坐落在缙云山角的一块缓坡地上,其前庭和后院有5米多的高差。
原先的总体规划也被调整了,将中轴线一直延长到园区的入口。从那里的一块绿地开始,来访的客人步行400米后,最终将在叠落水池的水声中走上宽大的台阶,只见6层高的架空拱门居于中轴线上,透过他们可以看到青翠的缙云山景。房子以灰砖墙砌筑,底层有花岗石柱廊,顶上是中国传统的歇山灰瓦屋顶。在转角和房檐下,有浅黄色的墙面和木条装饰线,隐隐的传达出巴蜀独有的地方性建筑符号。如果访客对北碚比较熟悉,或许他会立即想起老西南大学里的红楼和科学院,那是1930年卢作孚先生聘请一位丹麦建筑师建造的。
目前,主楼方案已获政府领导层通过。施工图设计单位是当地的一家甲级设计院,我们正在配合,以便落实那些转折的墙面和木装饰条,还有大屋顶上的斜天窗的施工方法……
最后一句话:这个设计,可以算是对我的同龄人的一种反叛,也可以算是对我的前辈们的致敬。 |